2019-1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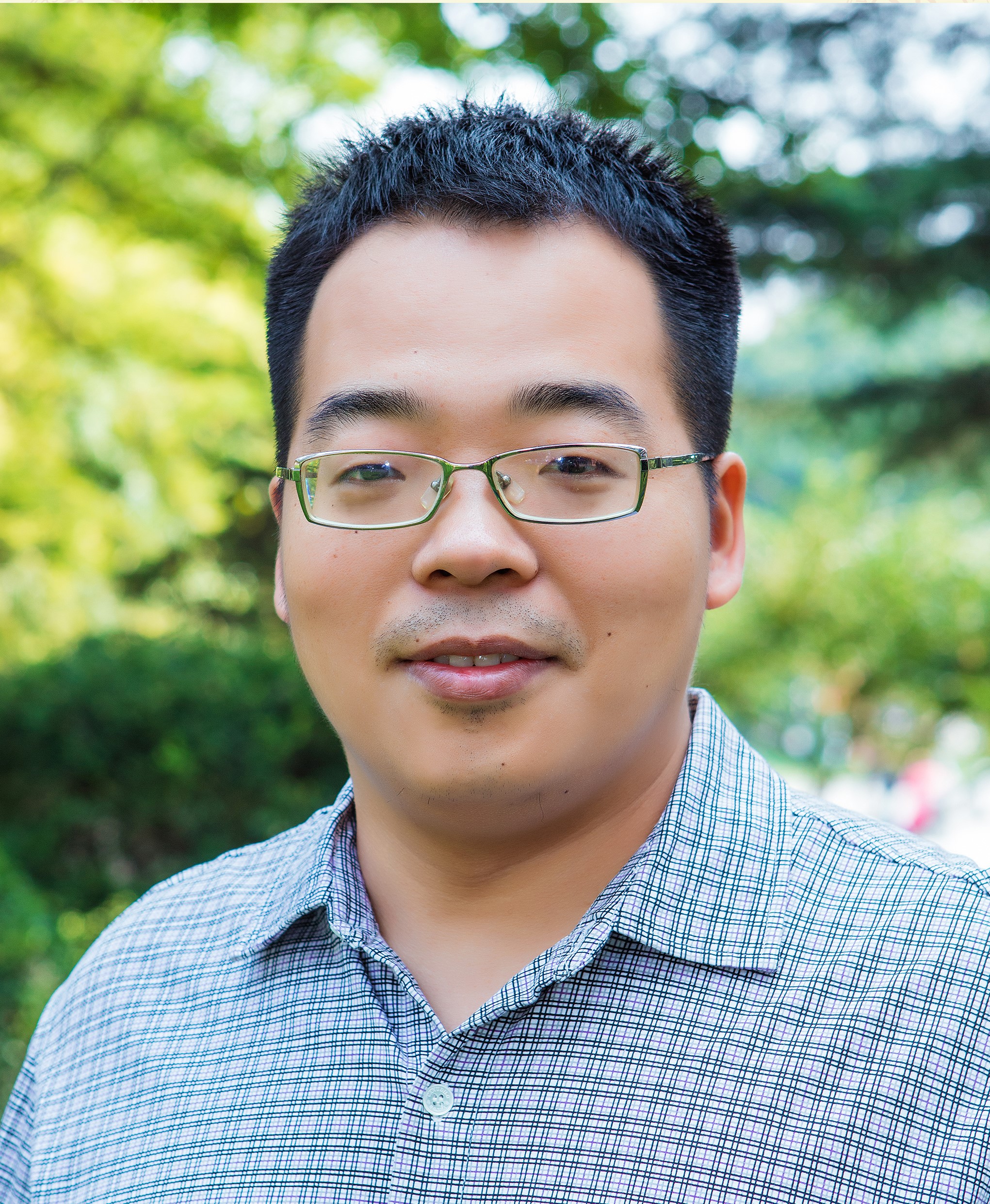
李文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治理质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城市治理和地方治理,都需要把基层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放到更为突出和重要位置。由于城市异质性、个体差异性和事务复杂性,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很多挑战和难题。把基层社会治理好,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它需要行动者具有较高的治理技艺。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我们常常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多关注细枝末节而忽略总体。为此,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从思考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出发,讨论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有序成长的核心议题,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知识的累积性发展和治理水平提升。
根本性问题是我们研究和思考的一种重要路径,但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将首都的核心功能定位为“四个中心”,这就是城市发展战略的根本性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性问题主要是处理基层社会中政权、人民和公共事务三者之间关系,其核心是建构管治、共治和自治的治理体系来满足人民对于公共服务提供、公共问题解决和公共空间形成的需求。这一根本性问题,可以具体表述为五个子问题,即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属性和价值平衡问题、基层社会中国家政权与基层政权关系问题、基层社会中共建共治共享问题、基层社会中自治问题、基层社会中集体行动的路径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属性和价值平衡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根本性问题,离不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属性的分析,更离不开对基层社会治理基本价值追求的探究。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不同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小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不同于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这是基层社会治理所发生的不同场景造成的。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民众素质水平的不同程度,也会面临着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这是基层社会治理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正是由于属性的差异性,不同城市即便面临着“同样”的根本性问题,也会在具体程度、表现形式和重点方面有差异。
总体而言,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属性至少体现在规则体系、共同体属性和物理生态系统三个方面。基层社会一定会受到一个国家和城市自身的治理系统和治理规则的影响,它是宏观叙事的微观承载体。这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可能在基层,但根源可能在国家和城市。
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处理人与事、服务和设施之间关系,这使得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基层社会中的共同体属性和物理生态系统影响。基层社会的单元可能是小区,可能是村区,可能是单位社区,还可能是社区、街区和镇区等。不同基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会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影响。基层社会除了聚集的人群存在差异之外,物理设施、服务系统和基础设施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老旧小区不同于新商品小区,老城社区不同于大型社区,不同社区不仅文化不同,物理生态系统也不同。
基层社会的多重属性,对治理构成了挑战。一方面,这使得不可能存在治理的“灵丹妙药”,用一种解决方案来应对所有问题,必须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价值之间进行有效平衡。另一方面,这些不同属性所产生的价值诉求可能存在冲突,国家价值、城市价值和基层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治理价值、文化价值和可持续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冲突,都需要进行协商和融合。
基层社会中国家政权与基层政权的协调和职责重构
基层社会中国家政权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子问题。在基层社会场域中,需要处理不同政权类型之间的关系和权责模式,既要避免“有限权力,无限责任”的难题,又要避免“独立王国”的困境。简而言之,国家政权需要通过适当方式介入基层,又要给予基层政权适当空间,使得国家政权和基层政权两方面积极性都得以展现。
针对这些问题、困境和难题,需要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政权和基层政权进行重新整合,以调整各自职责关系,以应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但是,如何建立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尤其是如何处理“一对多”和“多对一”之间关系,需要各个地方进行探索。
北京市在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中,建构了国家政权和基层政权有机融合的界面型基层政权体系,既发挥国家政权和基层政权各自的作用,又使得这两种政权以一种整体方式呈现。对于可以由街道来完成的事务,北京通过“赋权”和“增能”来实现,并且以街道大部制改革为基础,建立界面型职责体系以包容多样性权责清单。对于街道完成有困难的事项,需要专业化“条条”来完成的,北京市在加强和整合专业化力量的同时,创造“吹哨报到”机制来促进协同。对于基层社会中政府部门多样和协调的难题,北京还探索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来促进治理效能整合。
基层社会中共建共治共享的路径和方法
基层政权如何与社会有效互动,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个子问题。政权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是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治理最关键的评判标准。为了突出政府与社会之间合作,以及探索合作的方式与方法,治理研究者专门提出了合作治理理论来描述、诊断和推进治理中合作行为的发生。
政权与社会之间有效性互动,意味着需要告别政府的单方行动,将政府行为建立在更多的回应性、协商性和合作性基础之上,这也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政府的回应性,强调政权需要以民众需求为旨趣,及时对民众需求作出反应,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与民众需求相匹配。政府的协商性,强调政权在问题解决和治理中要“问计于民”,无论是需求发现、问题建构,还是问题解决,都应该是官民协商的结果,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政府的合作性是对协商性的深化,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民众共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合作生产和合作治理是其表现形式。
共建共治共享作为一种理念,描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理想蓝图,但现实中需要找到实现路径和方法。北京市在推进共建共治共享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比较典型的是建立小巷管家、接诉即办和问计于民等。小巷管家的建立,让市民能够随时找到政府,并且能够让政府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发现问题。小巷管家涉及政府官员、社区工作者和民众等多样性人群,是一个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努力。接诉即办则是问需与民的具体体现,让市民通过12345热线能够直接找到政府,这是一个问题发现的过程。问计于民是政府与民众一起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北京通过建立居民对话会、六方协商等方式来促进共同行动。
基层社会中自治的培育和生长
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前提是政府和社会相对分离。基层社会自治的培育和生长是第四个子问题。基层社会自治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很多具体的问题,如邻里纠纷、环境改造、社区营造等由居民自己来完成。自治就需要激发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性,使得市民能够形成公共精神,实现公共问题的自我解决。
实现基层社会自治,可先通过具体事项的自主治理,让市民感受自主治理的魅力,懂得自主治理的技艺,形成自主治理的习性。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政府固然可以为加装电梯提供财政补助,但是否安装需要征求所在楼层居民的同意。在小区治理中,还存在很多类似电梯安装的公共事务需要通过自治方式来解决。
自主治理的培育和生长需要时间,也具有非对称性和脆弱性等特点。自主治理首先意味着个人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到公共事务之中,避免个人的自私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但是,最难改变的是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只有实现了成功的自主治理,才能够形成“正反馈”,并使得自主治理成为一种习惯。而自主治理成功之后,还需要使得自主治理具有可持续性,这是自主治理最大的挑战。北京在老旧小区治理和老城更新治理中,有很多这样的探索,政府通过一些具体公共事务的推动,克服居民自主治理的障碍。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制度、技术和文化保障
从根本上看,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集体行动过程。但集体行动会面临搭便车、过度使用等难题,从而形成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成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持续挑战。当前而言,促进基层集体行动的路径至少存在制度、技术和文化三种方案。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人类行为的规则系统,它禁止、允许和强制人们可以或者不可以从事某种行为。良好的治理成长总是与制度成长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的核心思想。为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北京市非常重视制度化的解决方案,通过制度供给为基层社会治理有效运行提供规则。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北京出台了《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这成为规范和约束街道办事处运行的最高级别规章。此外,针对反应比较多的物业难题,北京市正在就《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技术是促进集体行动的重要手段,提供了集体行动的平台,这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更为关键。技术也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为个人展开集体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技术促进集体行动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也发生在机构之间和组织之间,技术平台有利于整合不同组织机构的行动。北京市的网络管理平台、接诉即办平台等都是技术促进集体行动的典型,很多公共服务通过互联网等技术得以集成。
文化是集体行动得以产生的规范性因素,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可持续的基础。不同的小区面临着不同的物理环境、人群属性和公共问题情景,这也使得这些治理共同体在解决问题时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非正式规范、社会资本和文化。制度是一种刚性约束,文化是一种软性约束,两者在不同情景中发挥着不同作用,相互促进,相互配合。事实上,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也需要将文化与各种情景结合,而形成有利于治理质量提升和成长的文化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